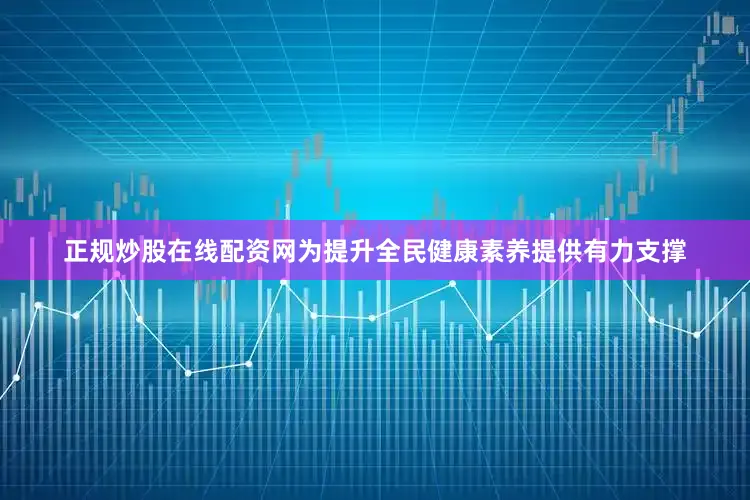1.
林溪的左腿,在五年前那场大雨中的追尾事故后,就落了点毛病。
骨头接好了,筋也拉顺了,走平路看不出大问题,只是步伐略微有些涩滞,细细品咂,能觉出一点儿不协调的“硌”。
一旦快走、上楼、或者天气阴沉关节酸胀时,那点不协调就会放大,变成轻微的跛行——像光滑的瓷器上那道细细的、不易察觉却确实存在的裂纹。
她今年三十,在一家不大不小的广告公司做着设计助理,月入四千,在南方这座消费不低的城市里,精打细算着过活。
工作谈不上稳定,公司效益时好时坏,随时可能被优化的阴影如同角落里结网的蜘蛛,总在不经意间提醒着她的处境。
父母在老家小城,退休金微薄,最大的心愿就是她这个“大龄”“腿脚还不算太利索”的女儿能嫁个好人家。相亲,是林溪生活里的常态。
遇见周辰,是在“幸福鹊桥”的线下联谊会上。三十五岁的周辰,在一家大型科技公司做部门经理,体面,稳定,月薪三万多。
介绍人红姨的语气里带着十二分的推介:“小周可是个宝,人稳重,条件顶顶好,就是挑了点……” 言下之意,林溪能进入“候选”名单,已是红姨努力撮合的结果。
联谊会灯光柔和,自助餐点精致。林溪穿着特意买的新裙子,鞋子选了软底低跟,小心掩饰着步伐。她习惯了在人群里尽量降低存在感,坐在角落小口吃着水果。
周辰端着香槟杯和几个男士谈笑,他个子很高,肩膀宽阔,戴着无框眼镜,有一种笃定沉静的气质。目光偶然扫过角落的林溪,略作停留,竟穿过人群,径直向她走来。
“你好,林小姐?听红姨提过。”声音温和,带着恰到好处的距离感。
林溪局促地起身,左脚踝习惯性地微屈,稳住重心:“周先生好。”
“在XX广告?”周辰似乎提前看过资料。
“嗯,做设计助理。”林溪答得有些心虚。助理,离“设计师”似乎总差着一口气。
“很有创造力的工作。”周辰笑了笑,目光落在她身上,带着审视,但不算失礼。“这里有点吵,要不要去外面露台聊聊?”
那次聊了足有四十分钟。周辰话不多,但每句都落在点上。他不问腿疾,不问收入,聊起城市的变化,聊他刚看的一部科幻小说,也问了林溪对设计的一些看法。
林溪起初紧张,后来被他的思路带着,竟也放松下来,表达了一些自己的想法。他的目光专注,让人感觉被重视。
结束时,他掏出手机:“留个联系方式?”
第一次见面,林溪是坐公交回去的。车窗映着她微微发热的脸颊。她知道自己身上那道无形的“裂纹”,在相亲市场上是明晃晃的减分项。
周辰的主动和礼貌,像一缕阳光照进她灰扑扑的生活,带来一种虚幻又无比真实的暖意。他太耀眼了,耀眼得让她觉得能被他看一眼,都是一种额外的恩赐。
2.
交往比预想中顺利。周辰工作很忙,但固定每周见一次。
约会地点多是环境清雅的餐厅,人均消费对林溪而言算奢侈。
起初她也想AA,周辰摆摆手:“别客气,我请你。”语气温和,却有种不容置喙的肯定,将那点客气的缝隙也堵上了。林溪心里有点涩,但更多的是被照顾的熨帖。
他确实是个很好的交往对象。举止得体,谈吐不俗,没有过分热情,却也从不敷衍。
他会帮她拉椅子,过马路时下意识靠近车辆来的那一侧——这些小细节像细密的针脚,缝补着林溪因腿疾和处境而有些龟裂的自尊。
他极少谈及她的工作,只在一次送她回家,看到她挤在破旧楼道里时,皱了下眉:“这地方环境不太好,安全吗?”
林溪窘迫地低着头:“还好…习惯了。”心里某个地方像被刺了一下。
他也带她去见过他那圈子的朋友聚会。聚会上的人体面光鲜,话题围绕着买房、投资、国外游学。林溪安静地坐着,努力保持微笑,脚踝在灯光下,似乎也隐隐作痛起来。
她能感觉到那些人目光中一闪而过的、带着礼貌掩饰的探究。她插不进话题,偶尔开口,也只限于回答“嗯”、“是的”。
周辰会适时地递给她剥好的水果,看似体贴,却更让她觉得自己像个需要被照顾的局外人。
有一次,两人看完电影出来,穿过一条不平整的人行道。林溪没注意一个凹陷的小坑,脚一崴,身体瞬间失衡。
周辰眼疾手快一把扶住了她,她的重量几乎全压在他手臂上。站稳时,林溪脸色煞白,呼吸急促,不仅是吓的,更是那种狼狈暴露无遗的羞耻感。
“小心点。”周辰把她扶正,语气平稳,但扶着她手臂的手很快放开了。
“嗯…谢谢。”林溪低着头,声音发颤。那一路上,两人沉默了许多。那道看不见的裂纹,在那一刻仿佛裂开了更大的缝隙。
她变得患得患失。他的一条消息久未回复,她会反复看手机;约会时,他偶尔的走神,也会让她心头发紧。
她知道自己条件与他差距太大,唯一的依仗,似乎就是他目前还愿意延续这份关系。这份认知,让她在这场关系里,腰杆总也直不起来。
她开始更关注他的喜好,记下他随口提过想看的书,省下半个月工资买下放在他办公桌上当“惊喜”;他顺口说一句某家新开的川菜不错,她立刻去研究攻略,预约好位置等他周末光临。
她像个勤恳的园丁,小心翼翼地捧着自己这片可能随时倾塌的花园。
3.
交往半年。一个周末,周辰送林溪回家,没像往常一样送到楼下就走,而是少见地说:“上去坐坐吧,叔叔阿姨在家吗?”
林溪心头一跳。她父母是特意从老家赶来的,名义上是看看女儿,实质是带着任务——探探男方的“诚意”。
逼仄的老旧一居室里,林溪父母热情得有些局促。寒暄过后,话题很快滑向正轨。
林父搓着手,脸上是堆出来的笑:“小周啊,你看,你和溪溪也处了这么久,我们当父母的也放心。你们年纪都不小了,这婚事儿,是不是也该考虑起来了?”
林溪紧张地看着周辰。周辰神色自若,点了点头:“叔叔阿姨说的是。”
林母趁热打铁:“按我们老家的规矩,还有溪溪这情况…我们商量了下,这彩礼呢,图个吉利好彩头,28万。”她刻意加重了“这情况”三个字,眼睛瞥了一下林溪搁在沙发扶手上的左腿,又飞快看向周辰。
空气瞬间凝滞。林溪的心猛地一沉,几乎喘不过气。
28万!这个数字把她自己也惊到了。她知道老家有彩礼风俗,但没想到父母会在这个节骨眼上开出这样的价码。
周辰脸上的温和迅速褪去,换上了一层薄冰似的疏离。他端起茶几上那杯廉价的茶水,抿了一口,再放下,动作很慢,慢得令人窒息。
他抬眼,目光平静地扫过林溪,最后落在林溪父母脸上,声音里听不出喜怒:“叔叔阿姨,这个数目,恕我难以接受。我理解老家的规矩,但结婚是两个人新生活的开始,需要的是实际规划和互相理解,我个人觉得,彩礼的意义应该在这个前提下重新衡量。”
林父脸上的笑容僵住了:“小周,话不能这么说,这钱也是给小家庭一个新婚的保障,我们养大溪溪也不容易…”
“是啊是啊,”林母帮腔,话里有话,“我们家溪溪,模样性子都是顶好的,就是腿脚当年出了事,吃了苦头…” 潜台词不言而喻:我们是“吃亏”的。
周辰的嘴角极其轻微地向下压了一下。这个细微的动作被林溪捕捉到了,像针扎一样疼。他终于直接点到了那块“裂纹”。
“抱歉,叔叔阿姨。”周辰站起身,语气恢复了惯常的沉稳礼貌,但那份疏离感更重了,“我突然想起公司还有点事要处理,得先走了。彩礼的事,我需要和我父母商量一下。林溪,我先走了。”他甚至没有多看林溪一眼,径自开门离去。
门关上的那声轻响,像一把重锤砸在林溪心口。客厅里死寂一片,只有父母面面相觑和不满的嘟囔声:“这什么态度…” “28万算多吗?现在这行情…”
林溪只觉得一阵巨大的眩晕袭来,五年前车祸时那种天旋地转的感觉又回来了。她的春天,可能还没真正舒展枝叶,就要被这场突如其来的冰雹砸得七零八落了。
4.
接下来的日子,林溪陷入了无边的焦虑。周辰没有主动联系她。她鼓起勇气打去电话,响了好多声才接,背景音是键盘敲击声。
“喂?”声音平静,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。
“周辰…我爸妈那天说的话…”林溪喉咙发紧,声音干涩,“他们也是为我好,但那个彩礼…其实可以…”
“林溪,”周辰打断她,声音异常冷静清晰,“我父母知道了彩礼的事,还有其他一些情况。”
林溪的心瞬间提到嗓子眼。
“他们对28万的数额非常意外。另外,”他停顿了一下,那短暂的沉默如同钝刀割肉,“他们对你的身体状况和…经济能力,也有顾虑。认为不太适合组建家庭。”
每一个字,都像冰雹砸在脸上。林溪握着手机的手指冰冷僵硬,几乎失去知觉。
他父母的顾虑!他把她最深的隐痛和最不堪的现实,赤裸裸地摊开在她面前。那道裂纹,终究被毫不留情地撕开了。
“那…那你呢?”她声音颤抖得不成样子,指甲深深掐进掌心。
电话那端沉默了几秒,时间长得令人窒息。“林溪,”他再次开口,语气里有一种残忍的平和,“我们开始得很美好,但婚姻和恋爱不同,它牵涉两个家庭,更关乎长久的现实支撑和共同承担。我父母的意见…我不能完全无视。况且,”他似乎斟酌了一下用词,“我们之间的差距,包括生活习惯、未来规划,可能比我们最初想象的更大一些。所以…我想,我们可能还是不太合适。”
“不合适”。
轻飘飘的三个字,将她半年来小心维护的自尊、期冀,以及那一点点刚燃起的关于“配得上”的妄想,击得粉碎。他连一句“我不在意”的假意安慰都没有。
“就因为…就因为我的腿?还有钱?”林溪的泪水终于控制不住,冲口而出,带着崩溃和质问,“我可以不要那么多彩礼!我爸妈那边我去说!只要…”只要你别放弃我。后半句被她生生咽了回去,变成了绝望的呜咽。
“林溪,别这样。”周辰的声音里终于透出一点不耐烦,“这和彩礼数额不完全相关,是我们之间本身存在的问题。我们不合适,真的。强扭的瓜不甜。祝你以后找到更合适的人。” 他的冷静和客套,在此刻像最锋利的刀子。
“周辰!”林溪对着挂断的电话嘶喊,回应她的只有冰冷的忙音。
5.
林溪的世界崩塌了。她无法接受这个判决。
在她看来,周辰就是她能遇到的最好归宿,错过了他,以她的条件,可能这辈子就这样了。恐惧如同冰冷的海水,将她彻底淹没。
她开始了卑微到尘埃里的挽回。
她给他发长长的信息,字字泣血:道歉父母的无理要求,承诺彩礼一分钱可以不要;剖析自己的情意,尽管连她自己都知道这情意有多复杂(多少混杂着对安稳和“得救”的渴望);甚至隐晦地提及自己的“缺陷”,恳求他的怜悯和不弃:“我知道自己不够好,配不上你,我可以改,我以后会更努力…求你再给我们一次机会…”
她去找红姨,哭得几乎晕厥,求红姨再帮忙说说情。红姨为难地叹气:“溪丫头,小周那态度很坚决了,他父母那一关更是…哎,你这腿脚和收入,在人家那种家庭眼里,确实是道坎…”
她跑到周辰公司楼下等他。初夏的天气,她穿着单薄的裙子,在带着湿气的风里站了三小时,腿隐隐作痛。
周辰的车开出来,她扑过去拍车窗。车窗缓缓降下一条缝,露出他紧蹙的眉头和毫无温度的眼睛。
“林溪,请自重。我们已经结束了,你这样,只会让我们彼此更难堪。”他的声音冰冷得没有一丝波澜。
“周辰,我们谈谈好不好?就最后谈一次!我保证…”林溪的声音带着哭腔。
“该说的都说清楚了。”车窗升起,车子毫不犹豫地驶离,将她和她满心的狼狈一同甩在原地。
所有的信息都石沉大海。所有的哀求都如同投入深海的石子,连个回声都没有。
周辰的绝情,像一盆兜头浇下的冰水,终于让她在刺骨的寒冷中清醒了一丝。
她看着镜子里那个眼泡红肿、面容憔悴、因为连日失眠和哭泣显得比实际年龄苍老了好几岁的女人,那个因为极度恐惧失去“好归宿”而把自己低到泥土里的女人,陌生得让她心惊。
那个曾经在联谊会角落里安静吃水果、面对他也能表达自己想法的林溪,去哪里了?
一个闷热的午后,林溪的手机响了。屏幕上跳动着“周辰”的名字。她的心骤然狂跳,手忙脚乱地接通,声音都在发抖:“喂?周辰?”
“林溪,”周辰的声音隔着电波传来,依然清晰,冷静,带着一种公事公办的疏离,“是我。别再给我发信息打电话了。我们不合适,结束是理智的选择。纠缠没有任何意义。希望你以后过得好。再见。”
“嘟嘟嘟……”
这次连一个象征性的“祝福”都省了。他只是来斩断最后一丝她可能还抱着的念想。彻底的,不留余地的。
林溪握着手机,听着里面传来的忙音,一动不动地站在狭小的出租屋里。窗外是城市永不停歇的车流声。有光透过窗格,在地上投下摇晃的碎影。
她脸上的泪早已干涸,只留下紧绷的不适感。心口像是被掏空了一大块,风呼呼地灌进来,吹得她四肢百骸都冰凉麻木。
她终于明白,那些信息,那些电话,那些卑微的纠缠,在他眼里,不过是一个她不愿认清现实的、纠缠不休的“包袱”。她的痛楚她的绝望她的挽留,只感动了她自己。
那条腿,那点工资,连同她自认为能抓住救命稻草的决心和卑微,都成了他眼中无法忽视的“问题”,成为他可以毫不犹豫松手的理由。
“缘分?哈。”林溪对着冰冷的空气,发出一声短促、嘶哑、不知是哭还是笑的声响。
是啊,多么轻飘飘的理由——“没缘分”。
他用这世俗的砝码衡量她,精准地在她那头加上了“身体缺陷”、“收入低微”、“原生家庭无理要求”的沉重砝码,然后理所当然地宣布:不平衡,不合适,所以没缘分。
这“缘分”的轻与重,原来早就标好了价码。
6.
林溪病了一场。或许是心火攻心,或许是淋了雨,连续几天高烧不退,浑身酸痛。
一个人躺在出租屋那张小小的床上,裹着厚被子,汗湿了又干,干了又湿。
意识模糊时,五年前车祸后躺在医院那漫长的恢复期又浮现在眼前,也是这样的无助、痛苦和对未来深深的茫然。
不同的是,那时有父母的焦急和医生的鼓励。而现在,只有她自己,和窗外那漠然流动的城市光影。
退了烧,身体依旧虚弱,但脑袋像是被这场高烧烧透了,灼烧掉了许多粘连不清的东西。
她挣扎着起床,拉开窗帘。初夏午后的阳光带着一点白炽的力度,刺得她眼睛生疼。她看到楼下街角那个开了十几年、毫不起眼的裁缝铺。
店主王阿姨是个寡居的女人,总佝偻着背,手指却灵巧得能在缝纫机上绣花。
林溪记得,自己刚搬来时,有条裤子太长,拿到王阿姨那里改短。
王阿姨接过裤子,看了看她的腿,一句话也没问,只细心地量了她的腿长,然后默默地帮她把左腿裤脚比右腿裤脚多收了微不可察的半厘米。
“孩子,走路舒坦最重要。”改好裤子那天,王阿姨递给她,脸上是淡淡的笑意,眼神里是看透世事的包容。
那一刻的善意和尊重,像一道微弱却坚定的光,此刻在林溪心里缓缓复苏。
她打开手机。之前像魔怔般记录关于周辰喜好的备忘录,那些精心编辑却没发出去的消息草稿,统统被她删除了。
她点开被冷落许久的工作群,里面正为一个紧急的项目手忙脚乱。她深吸一口气,敲下一行字:“王总,那个XX项目的视觉草图,我退烧好点了,今天在家能赶出来,晚上发您初稿。”
手指发出这条信息时,带起一阵轻微的酸麻。但删掉周辰所有联系方式时,心里那片巨大的空洞,似乎也并没有想象中那样深不见底。
她开始慢慢走回自己的生活轨道。上班,加班,做那些似乎永远也做不完的设计图。
工作依旧不稳定,工资也还是四千,但当她坐在电脑前,专注于线条和色彩,把甲方那些挑剔的要求一点点变成落地的方案时,她感受到一种奇异的平静——一种脚踏实地的、只属于她自己的价值感在一点点滋生。
脚踝还是会酸胀,走路依旧有那点“硌”的感觉。可那不再是她时时刻刻想着去掩饰的“裂纹”,而是她经历的一部分,是她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、抗争过、活着的证明。
她不再刻意掩饰,走路时腰板反倒不知不觉挺直了些。
秋天快结束的时候,林溪因为工作结识了一个开独立工作室的女插画师。两人聊得投机,对方欣赏她对色彩和细节的敏感度,邀请她加入一个小的插画项目。项目虽小,报酬也一般,但充满新鲜的挑战和创作的自由。
一次项目讨论后,她们在一个老街区咖啡馆闲坐。聊着聊着,女插画师看着窗外步履匆匆的人群,忽然感慨:“林溪,你知道吗?我最羡慕你的,是你身上有种钝感力。就是那种,被生活捶打过了,但好像还能不慌不忙,有股韧劲儿。”
钝感力?林溪愣了一下,搅动着杯里凉掉的咖啡,笑了笑。
她想起那个闷热午后,握着手机站在空屋子里的自己。被生活狠狠捶打的时刻怎么少得了?只是那一次次的捶打,好像真的把那点钻心的疼,那点深入骨髓的害怕,那点因“不配”而产生的战战兢兢,都磨掉了一些棱角。
取而代之的,是一种更为厚重的、沉默的接纳——接纳自己的不完美,接纳世事无常,接纳所谓“好归宿”的幻想破灭后,生活本身那粗粝的真实和可能拥有的微小光亮。
窗外的阳光穿过梧桐树光秃的枝桠,斜斜地照在她搁在桌面微微跛着的左脚踝上。那道疤,在阳光下显得很淡,却也无比清晰。
它还在那里。而她,已经不再需要谁来证明,她是否值得被爱,被珍惜。
她缓慢地、甚至带着点跛足地,走在她自己的春天里。这个春天或许迟了些,风里还有些寒意,但它终究是来了。
加杠杆炒股票.配资投资平台.股市五倍杠杆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