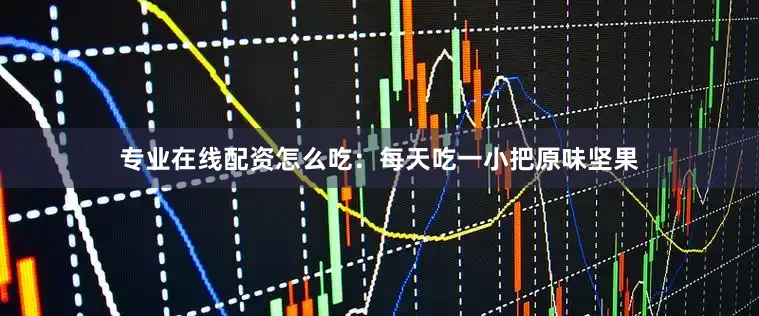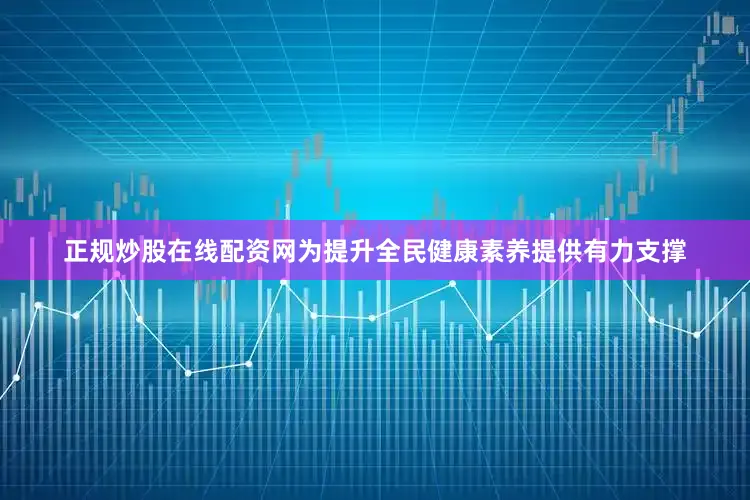【虚构声明:本故事纯属虚构,如有雷同,纯属巧合。】
“我与那汉高祖,究竟谁更强些?”宋公刘裕问。酒气混着血气的大帐里,一瞬间静得只剩下火盆里炭火的爆裂声。百战功成的将军们面面相觑,无人敢先答。只有一个角落里,传来一声极轻的冷笑,像一根冰针,刺破了这团滚烫的寂静。
01
东晋义熙十三年的秋天,来得特别早,也特别冷。
广固城刚被攻下没几天,城头上的血迹被秋风一吹,凝成了暗红色的痂。风里带着一股铁锈和腐肉混合的怪味,怎么也散不掉。
宋公刘裕的大营,就驻扎在城外五里处,像一头征服了猎物的巨兽,匍匐在齐鲁大地上,喘着粗气。白天,这里是军令如山的钢铁森林;到了晚上,卸下甲胄,就成了用大块吃肉、大碗喝酒来稀释死亡阴影的男人世界。
最大的那顶主帅营帐,是这片钢铁森林的心脏。几十个巨大的火盆烧得通红,把将军们一张张饱经风霜的脸映照得如同庙里的怒目金刚。他们中的大多数,都是当年跟着刘裕从京口赤手空拳闯出来的老兄弟,是那种可以在战场上为你挡刀,也可以在酒桌上指着你鼻子骂娘的交情。
他们喝酒,不用杯,用碗。碗是粗瓷的,从南燕国库里缴获来的,碗沿上还带着磕碰的豁口。他们喝酒的样子,像是在喝仇人的血,仰起脖子,喉结滚动,一饮而尽,然后把碗重重地砸在案几上,发出“砰”的闷响,像是为一场杀戮画上句号。
刘裕坐在主位。他已经五十五岁了,两鬓染霜,眼角的皱纹深得能夹死蚊子。但他坐在那里,腰杆挺得像一杆插在地里的长矛,岁月没能磨掉他的锐气,反而把他磨成了一把更加内敛、也更加危险的古刃。他没穿那身象征“宋公”显赫身份的朝服,依旧是一身洗得发白的布甲,只是卸去了肩上沉重的甲片,露出了里面被汗水浸透的粗布中衣。
他喝酒的样子,比任何人都要猛。那不是品尝,而是吞咽,仿佛只有最烈的酒,才能压下他心中那股翻腾不休的火焰。那火焰里,有对过往贫贱的记忆,有对生死无常的感慨,更有对未来的、连他自己都不敢深想的渴望。
王镇恶,那位继承了先祖王猛风骨的悍将,正抱着一只烤得滋滋冒油的羊腿,啃得满脸油光。他一边撕咬着焦黄的羊肉,一边含混不清地对身边的亲兵吼道:“酒呢?老子的酒坛子空了!再搬一坛来!今晚不把宋公灌趴下,谁也别想走!”

檀道济坐在他的对面,动作要斯文许多。他用小刀,慢条斯理地片下羊肉,再小口地喝酒。他的目光比帐中所有人都沉静,像一口幽深的古井,井水里倒映着这满帐的喧嚣、火光和人影,却不起一丝波澜。他看着狂放的王镇恶,看着豪饮的刘裕,看着这群暂时忘记了伤痛和死亡的汉子,心里明白,战争这头怪兽,只是暂时睡着了。
刘裕又喝干了一碗。他放下碗,目光缓缓扫过帐下的一张张脸。刘敬宣、向靖、朱龄石……这些名字,每一个都代表着一场血战,代表着一段用命换来的功勋。这是他的家底,是他从一个在街头卖草鞋、时常食不果腹的孤儿,一步步走到今天,能让司马家的皇帝都夜不能寐的本钱。
一股混杂着酒精和权力的豪情,从他胸中升腾而起。他忽然想起了史书上浓墨重彩的那个人。那个和他一样,从社会最底层爬起来,最终提着三尺剑,把整个天下都握在手心里的男人。
“你们都说说看,”刘裕的声音并不高,甚至有些沙哑,但在这片喧闹中,却像一块巨石砸入池塘,瞬间激起千层浪,又瞬间让一切归于沉寂,“我刘裕,比起四百多年前的汉高祖刘邦,孰强孰弱?”
这个问题,像一道闪电,劈开了帐内的混沌。
将军们脸上的醉意,一下子被惊醒了大半。他们停下了吃肉的嘴,放下了喝酒的碗,彼此交换着眼神。这是一个陷阱,也是一个机会。谁都知道标准答案是什么,但第一个开口的人,需要拿捏好分寸。这马屁不能拍得太轻,也不能拍得太重,更不能拍在马腿上。
王镇恶把啃得只剩骨头的羊腿往桌案上“哐”地一扔,溅起点点油星。他抹了把嘴,第一个站了起来,他那与生俱来的大嗓门,像平地起了一阵惊雷:“这还用比吗?宋公您,自然是远胜汉高祖百倍!”
他开了这个头,气氛立刻就被点燃了。
“王将军说得对!”另一位黑脸将军也站起身,因为激动和酒精,脖子上的青筋都爆了起来,“汉高祖算个什么?他不过是命好,恰巧碰上了秦朝末年天下大乱,是个男人都敢扯杆旗子造反。他身边又有萧何、韩信、张良这帮人辅佐。咱们宋公,那可是硬生生从太平世道里,一刀一枪,从尸山血海中杀出一条血路来的!”
“正是!论带兵打仗,汉高祖哪是项羽的对手?彭城一战,几十万大军被项羽三万骑兵冲得七零八落,连老婆老爹都丢了,何其狼狈!咱们宋公呢?无论是平定妖贼孙恩,还是讨伐国贼桓玄,还是这次北伐南燕,哪一次不是身先士卒,亲冒矢石?哪一次不是把敌人打得闻风丧胆,望风而降?”
“要我说,汉高祖就是个市井无赖,靠着耍手段、会用人得了天下。咱们宋公,才是顶天立地,凭着一身真本事打天下的真英雄!”
赞美之词,如同不要钱的潮水,一浪高过一浪。每一句话,都像是温暖的羽毛,轻轻搔刮着刘裕的心。他紧绷的脸部线条,不自觉地柔和了下来,嘴角勾起一丝几乎看不见的笑意。他享受这种比较,更享受这种结论。
他确实觉得自己比刘邦强。
刘邦打天下时,对手虽然强大,但目标明确。而他刘裕,一路走来,敌人来自四面八方。有朝堂之上的士族门阀,有手握兵权的同僚,有割据一方的枭雄,还有他自己心里那个时常会冒出来的,对前途的迷茫。
他端起一碗新添的酒,准备一饮而尽,将这满帐的颂扬,连同胜利的果实,一起吞入腹中。
就在此时,一个极不和谐的声音,从大帐最不起眼的角落里,幽幽地传了出来。
“宋公比汉高祖,差得远了。”
声音不大,甚至有些虚弱,但在这片阿谀奉承的热烈氛围里,却显得格外清晰,像一根淬了冰的钢针,狠狠地扎进了在场每一个人的耳膜。
02
仿佛有一只无形的大手,瞬间扼住了所有人的喉咙。
喧闹、笑语、咀嚼声、祝酒声……所有的一切,都在这一刹那戛然而止。将军们脸上的笑容僵住了,像是被冬日的寒风吹了三天三夜的劣质面具,滑稽而又诡异。连火盆里跳动的火焰,似乎都凝固了一瞬。
所有人的目光,像上百支离弦的箭,齐刷刷地射向了那个发出声音的角落。
那里,跪坐着十几个形容枯槁、衣衫破旧的人。他们是战败的南燕国的王公大臣,如今成了这场庆功宴上最卑微的点缀。在这场属于胜利者的狂欢里,他们像一群被遗忘在角落里的祭品,连呼吸都小心翼翼,生怕惊扰了神明。
说话的,是跪在最前面的一个中年人。
他约莫四十出头,面容清癯,颧骨高耸,嘴唇因为缺水而有些干裂。虽然身上穿着象征囚徒身份的粗麻布衣,但他的腰背,却挺得像一杆宁折不弯的竹子。他的眼神很平静,平静得不像一个刚刚经历了国破家亡的俘虏,倒像一个置身事外的看客。
刘裕的目光,像两把出鞘的利剑,裹挟着尸山血海中凝练出的杀气,直刺过去。他脸上的笑意早已荡然无存,取而代de的,是如同西伯利亚寒流般的冰冷。
“刚才的话,是你说的?”刘裕缓缓开口,每个字都像是从齿缝间挤出来的,带着金属摩擦的质感。
那个中年人抬起头,毫不畏惧地迎上刘裕的目光,平静地点了点头:“回宋公,是草民说的。”
“你是何人?”刘裕的声调没有起伏,却让帐内的温度又降了几分。
“草民慕容平,亡国之前,曾任南燕散骑常侍。”
慕容。这个姓氏本身,在晋人听来,就充满了背叛和仇恨。鲜卑慕容氏,从永嘉之乱开始,就与晋朝在中原大地上反复拉锯,纠缠了近百年,是刻在骨子里的死敌。
“大胆!”王镇恶“霍”地一声站起,腰间的环首刀随之作响。他指着慕容平,双目圆睁,怒骂道:“你这亡国之奴,死到临头,还敢在此妖言惑众,污蔑宋公!来人!把他给我拖出去,乱刀砍死喂狗!”
两名虎背熊腰的亲兵立刻应声上前,狞笑着伸手去抓慕容平的肩膀。
慕容平却连看都未看他们一眼,他的目光,如同一口被锁住的深井,始终倒映着刘裕一个人的身影。他没有挣扎,没有求饶,甚至没有一丝一毫的恐惧。
“且慢。”刘裕抬了抬手。那轻描淡写的一个动作,却仿佛有千钧之力,让那两名亲兵瞬间定在原地。
刘裕死死地盯着慕容平,他想从这个人的脸上,看出一丝虚张声势,或者一丝故作高深。但他什么都没有看到。只看到了坦然,一种洞悉了生死之后的、令人极不舒服的坦然。

这种眼神,他只在一种人身上见过——那些真正置生死于度外的死士。
“你说我,比汉高祖差得远了?”刘裕一字一顿地重复道,像是在确认一件荒诞到极点的事情。
“是。”慕容平的回答,只有一个字,干净利落,掷地有声。
“哈哈……哈哈哈哈!”刘裕忽然仰天大笑,笑声雄浑,震得帐顶的积尘簌簌落下。但帐中的每一个人,都从这笑声中听出了滔天的怒火。“好!好一个伶牙俐齿的亡国之臣!我刘裕起于布衣,提三尺剑,南征北战二十余载,扫平内乱,开拓疆土,自问功业,不输古之任何英雄。今天,我倒要洗耳恭听,你这个阶下之囚,能说出什么道理来!我究竟比那个只会跟人分一杯羹的刘邦,差在了哪里?”
他的笑声戛然而止,帐内的气氛瞬间压抑到了极点。所有人都明白,宋公是真的动了雷霆之怒。
檀道济站起身,对着刘裕深深一揖,沉声道:“宋公,不过是一个将死之人的疯言疯语,您何必与他一般见识?平白污了您的耳朵。不如让末将即刻将他斩首,以正视听,免得扰了大家的酒兴。”
檀道济这是在给刘裕台阶下。和一个必死的俘虏较真,赢了也不光彩,传出去,反倒显得刘裕气量狭小。
刘裕却摆了摆手。他今天,偏要较这个真。他要让这个人死得明明白白,也要让帐下所有将领都听得清清楚楚,他刘裕,到底是不是不如刘邦。
“不急。”刘裕的目光像鹰爪一样攫住慕容平,“让他说。我倒要听听,他这张嘴里,能吐出什么样的锦绣文章来。你说,我给你这个机会。但你记住了,你的每一句话,都在为你自己,也为你身后那十几口慕容家的族人,决定生死。说得好,我或许可以让你死得体面些。说得不好……”
刘裕没有把话说完,但那未尽之言里蕴含的血腥气,比任何直接的威胁都更加令人不寒而栗。
慕容平仿佛没有感受到这股几乎凝成实质的杀意,他对着刘裕,整理了一下破旧的衣衫,然后深深地、郑重地一拜。
“谢宋公赐言。”
他直起身,环顾了一下四周。那些刚才还慷慨激昂的将军们,此刻都用一种看死人的眼光看着他,眼神里混杂着轻蔑和一丝不易察觉的好奇。
他清了清有些干涩的喉咙,用一种不疾不徐的语调,缓缓开口。
“宋公若要与汉高祖比较,草民以为,可从三处着眼。一曰时势,二曰用人,三曰格局。”
他的声音,在这死寂的大帐里,清晰得如同金石相击,条理分明,逻辑严谨,仿佛他不是在一个随时可能人头落地的生死之地,而是在昔日南燕国的朝堂上,从容不迫地向君主奏对。
“愿闻其详。”刘裕从牙缝里挤出四个字,身体微微前倾,像一头准备扑杀猎物的猛虎。
03
“先说时势。”慕容平的声音沉稳依旧,仿佛在讲述一段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久远历史。“汉高祖起事于秦末,是秦失其鹿,天下共逐之。暴秦苛政猛于虎,早已天怒人怨,六国旧人,天下百姓,无不思变。高祖顺天应人,振臂一呼,天下英雄豪杰,闻风而影从。他要面对的,是一个已经烂到根子里的旧秩序,和一个虽勇猛却失尽人心的项羽。天下百姓苦秦久矣,人心思定。可以说,是时势,选择了高祖,推着他一步步走向了帝位。此所谓,时势造英雄。”
他在这里稍作停顿,给众人一个消化的时间,随即话锋一转,目光再次直视刘裕。
“而宋公您呢?”
“您起兵之时,大晋虽已偏安百年,江河日下,但国祚尚存,法统犹在,司马家的龙椅上,还坐着天子。您要面对的,不是一个共同的、明确的敌人,而是无数个盘根错节的对手。您要平定孙恩、卢循,此为内乱;您要讨伐桓玄篡逆,此为清君侧;您要北伐南燕,西征后秦,此为开拓疆土。您的每一次征战,名义上都是为国尽忠,但天下人,并非都感念您的功绩。尤其是在建康的朝堂之上,那些高门大姓,王谢世家,有多少人盼着您兵败身死?有多少人在背后给您下绊子,拖后腿?”
“高祖刘邦,是推倒一堵人人喊打的危墙。而您,是在一片长满了毒草和荆棘的废墟之上,一边清理毒草,一边与四面八方的野兽搏斗,艰难地为自己开辟出一块立足之地。单论时势之艰难,处境之复杂,您,远胜于汉高祖。”
这番话,听起来像是在极力抬举刘裕。帐下将军们紧绷的脸色,稍稍缓和了一些,甚至有人露出了认同的神色。王镇恶按在刀柄上的手,也松开了几分。
刘裕面无表情,只是用指节,在粗糙的木案上,轻轻地、有节奏地敲击着,发出“笃,笃,篤”的声响。每一下,都像是敲在人们的心坎上。

“继续说。”他冷冷地吐出三个字。
“再说用人。”慕容平的声音里,透出一丝锋利。“汉高祖有言:‘运筹帷幄之中,决胜千里之外,吾不如子房;镇国家,抚百姓,给馈饷,不绝粮道,吾不如萧何;连百万之军,战必胜,攻必取,吾不如韩信。’此三者,皆人杰也。高祖能用之,且信之,故能得天下。更重要的是,这三人,皆是在他微末之时便倾心追随,名为君臣,实为一起打天下的伙伴。刘邦离了他们,寸步难行。”
慕容平的目光,不着痕迹地扫过王镇恶、檀道济等一众将领的脸。
“而宋公您呢?”他的语气微微加重,“您帐下的诸位将军,如王镇恶、檀道济、刘敬宣,个个都是能征善战的当世猛将,冲锋陷阵,攻城拔寨,无不以一当十。但是,”
这个“但是”,让所有将军的心都提了起来。
“他们都是您的下属,是您一手提拔起来的部将。他们能做的,是无条件地执行您的命令,将您的意志贯彻到底。他们对您,是敬,是畏,是绝对的忠诚。但他们,给不了您张良那样的奇谋,也给不了您萧何那样的安稳后方。他们是您手中最锋利的刀,最坚固的盾,却是您意志的延伸,是您的臂膀,而不是您的大脑。”
“更关键的是,”慕容平的声音陡然拔高,直刺核心,“您的韩信,在哪里?不,您没有韩信,也不需要韩信。因为您自己,就是那个‘战必胜、攻必取’的绝世统帅!您既是高祖,也是韩信。您凡事亲力亲为,军国大事,皆出己断。这既是您无往不胜的根源,也是您最大的短处。因为您太强大了,强大到您的光芒遮蔽了所有人,强大到您不需要一个能与您并驾齐驱的伙伴。您习惯了自己一个人,扛起所有的事情。”
“所以,论对手下人才的倚重与放权,论君臣之间那种伙伴式的信任,您,不如汉高祖。”
这番话,字字诛心。
王镇恶等人刚刚缓和的脸色,瞬间又变得铁青。说他们不如张良、萧何,他们虽然不服,但也无法理直气壮地辩驳。但说宋公用人不如刘邦,这简直是当着所有人的面,狠狠地打了刘裕的脸。
大帐内的空气,再度凝固。那“笃笃笃”的敲击声,也停了。
“第三呢?”刘裕问,声音低沉得可怕,像暴风雨来临前,海面下的暗流。
慕容平深吸了一口气,他知道,接下来的话,将是压上他和他所有族人性命的最后一块砝码。
“第三,说格局。”
他的声音比刚才低沉了许多,却带着一种奇异的穿透力,仿佛能洞穿人心。
“汉高祖的格局,在于一个‘争’字,更在于一个‘给’字。”
“他与项羽争天下。这天下,是秦始皇用铁血统一过的天下。天下人的心里,是有一个‘大一统’的模糊影子的。所以,高祖的目标从一开始就无比明确,那就是恢复这个‘大一统’,他要的,是整个天下。这是他格局的‘大’。”
“而他的‘给’,则更为致命。他入关中,与民约法三章,这是给百姓安宁。他击败项羽后,大封功臣,一口气封了韩信、彭越、英布等七个异姓王。他毫不吝惜地把刚刚打下来的土地和人口,分给那些帮他打天下的人。虽然他后来又用各种手段,把这些异姓王一个个除掉,但在当时,他的‘给’,让天下英雄都看到了希望,都愿意为他卖命。他用最实际的利益,笼络了最复杂的人心。”
慕容平说到这里,微微停顿,目光如炬,直视着刘裕,仿佛要将他从里到外彻底看透。
“宋公,草民斗胆问一句,您能给您的功臣们什么?”
这个问题,像一把无形的、烧红的锥子,带着“嗤”的一声,狠狠地扎进了刘裕的心脏。
他能给什么?
官职?他给了,帐下诸将,哪个不是将军、太守?金钱?他给了,每次战后,赏赐从不吝啬。美女?府邸?他都给了。
可是,他能给他们“封王”吗?能把一州一郡的土地,连同上面的百姓,像切蛋糕一样,分给他们,让他们做那片土地上说一不二的主人吗?
不能。
他不敢,也不能。
东晋的天下,法理上还是司马家的。他刘裕现在,还只是一个权倾朝野的臣子。他今天敢封一个异姓王,明天,建康城里那些门阀士族就敢以此为借口,联合天下清流,群起而攻之,骂他是第二个王莽。
更重要的是,他自己,那个从京口泥泞中一步步爬出来的刘裕,那个心里藏着九五之尊野望的刘裕,也绝不允许自己这么做。
他的天下,是他一刀一枪,用命换来的。每一寸土地,都浸透着他自己和袍泽的血汗。他怎么可能,心甘情愿地把它分给别人?
卧榻之侧,岂容他人酣睡!
刘裕的沉默,比任何回答都更加响亮。
慕容平看懂了这沉默背后的一切。
“您看,”他继续说道,语气里带着一丝悲悯,“汉高祖可以毫不在乎地‘给’,因为他骨子里就是个‘无赖’,他不在乎那些礼法虚名,他只在乎最赤裸裸的利益交换。他用土地和王位,换来了天下。而您,宋公,您太在乎自己的羽毛,太在乎‘大义’的名分。您背负着‘晋臣’这个身份,这既是您号令天下的护身符,也是束缚您手脚的沉重枷锁。”
“所以,论格局之开阔,论手段之灵活,论笼络人心之不拘一格,您,远不如汉高祖。
慕容平说完了他论证的第三点,也是最致命的一点。他把刘裕与刘邦的比较,从时势的艰难,到用人的方式,再到格局的大小,层层剥茧,最终得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无法接受,却又隐隐觉得无法反驳的结论:刘裕,不如刘邦。
这已经不是在分析,而是在审判。当着刘裕所有心腹爱将的面,一个亡国之臣,将他们心目中战无不胜的神,拉下了神坛,剥去了英雄的光环,露出了那个被身份、时代和性格所重重束缚的、充满挣扎的凡人。
大帐之内,死一般的寂静。
连呼吸声都消失了。只剩下火盆里的木炭,在燃尽最后的生命时,发出的“毕剥”哀鸣。
王镇恶的手,早已死死地握住了刀柄,手背上青筋坟起,像一条条盘踞的怒龙。只要刘裕的一个眼神,甚至只是一个轻微的点头,他就会在下一刻扑上去,把这个巧舌如簧的家伙剁成肉酱。
檀道济的眉头,已经拧成了一个死结。他觉得慕容平死定了,大罗金仙下凡也救不了他。他现在唯一在想的,是如何收拾这个残局,如何才能在处死此人之后,最大限度地维护住宋公的颜面。
所有人的目光,都像被磁石吸引的铁屑,死死地钉在刘裕的身上。
刘裕依旧坐在那里,一动不动,像一尊在风雨中矗立了千年的石雕。他的脸,一半在火光的映照下忽明忽暗,一半隐藏在深沉的阴影里,让人看不清他的表情。
只有他那只放在案几上的手,已经紧紧地攥成了拳头。指节因为过度用力,而失去了血色,呈现出一种令人心悸的惨白。
一股被压抑到极致的怒火,正在他的胸膛里疯狂地酝酿、膨胀,仿佛一座即将毁灭一切的火山。
他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羞辱。
这种羞辱,甚至超过了少年时在京口赌坊里,被地痞无赖当众吊起来殴打的那个下午。因为身体的疼痛可以愈合,而灵魂被看穿的赤裸感,却无药可医。
最让他感到愤怒的,不是慕容平的冒犯,而是他知道,这个俘虏说的,每一个字,都像一把精准的手术刀,剖开表皮,切中了要害。
他无法反驳。
正因为无法反驳,所以才更加愤怒。
一个帝王,或是一个即将成为帝王的人,最不能容忍的,就是被人彻底看穿。尤其,是被一个敌人,一个亡国之奴,当着所有心腹手下的面,赤裸裸地看穿。
杀了他。
必须杀了他。
只有这个人的鲜血,才能洗刷这种深入骨髓的耻辱。
刘裕的眼底,杀机爆射而出。他缓缓地抬起了自己的右手。那只手,曾经指挥过千军万马,曾经亲手斩下过无数敌人的头颅。此刻,它只要轻轻一挥,就能决定一个生命的终结。
整个大帐的空气,都仿佛凝固成了琥珀。
慕容平看着刘裕那只缓缓抬起的手,他的脸上,没有丝毫的恐惧。他甚至,还露出了一丝……微笑。那是一种夹杂着悲哀、了然,甚至是一丝怜悯的,极其复杂的笑容。
他迎着刘裕的杀气,迎着那只悬在半空、代表着审判的手,再次开口。他的声音不大,却像一道划破暗夜的惊雷,在刘裕的脑海中轰然炸响。
“所以,草民才说,宋公您,比汉高祖差得远了。”
“但是……”
他故意拉长了语调,那笑容里,多了一丝神秘莫测的意味,像一个准备揭开终极谜底的智者。
“那只是因为,您和汉高祖,从根子上,就不是一种人。您要走的路,和他截然不同。您要成就的功业,也远非他所能比拟。草民刚才所说的,只是您的‘短处’,却还未曾说及您的‘长处’。而您的‘长处’,恰恰是汉高祖,乃至历朝历代的开国之君,都梦寐以求,却无人能及的!”
刘裕那只抬到一半的手,猛地停在了半空中。
他像一尊被雷电劈中的雕像,死死地定在那里。
那座即将喷发的火山,在岩浆冲破地壳的最后一刻,被一股更加强大、更加无法抗拒的力量,硬生生地压了回去。
那股力量,叫做“好奇”,也叫做“野心”。
他想知道。
他迫切地想知道,这个已经半只脚踏入鬼门关的人,到底还能说出什么惊世骇俗的话来。
他更想知道,自己身上,到底有什么“长处”,是连那个开创了大汉四百年基业的汉高祖刘邦,都比不上的。
这个诱惑,实在太大了。大到足以让他暂时压下那焚心蚀骨的杀意和耻辱感。
慕容平看着刘裕停在半空的手,他知道,自己赌赢了最关键的一步。他先是将刘裕高高地捧起,再狠狠地摔下,现在,他要做的,是把他捧上一个前所未有的,连刘裕自己都未曾敢想象的,真正属于他自己的神坛。
他微微一笑,从容地整理了一下破烂的衣襟,仿佛接下来要说的,不是为自己求活的几句话,而是一个将要改变历史走向的惊天秘密。帐中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,他们隐约感觉到,今晚的这场对话,或许将成为一个传奇的开端,而他们,都是这个传奇的见证者。
04
大帐之内,所有人的心都悬在了嗓子眼。刘裕那只停在半空的手,像一尊审判的雕像,充满了不确定的威压。时间仿佛在这一刻被拉长,每一息都像一年那么漫长。

慕容平却像是没有看见那只足以决定他生死的手。他挺直了身子,目光清澈,仿佛一个胸有成竹的棋手,准备落下决定胜负的最后一子。
“草民斗胆,先问宋公一个问题。”慕容平的声音,将所有人的注意力都拉了回来,“宋公戎马一生,每收复一地,每打下一城,您是如何处置那些土地和人口的?”
这个问题,问得有些突兀,似乎与之前的话题毫不相干。
刘裕眉头一皱,没有立刻开口。他在审视,在判断。
旁边的王镇恶有些沉不住气了,他觉得这是一个表现的机会,替刘裕答道:“这还用问?自然是清查田亩,丈量土地,将流民和原住民一并编入户籍,纳入我大晋版图,由朝廷派遣官吏,统一管辖!”
慕容平听完,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容,那笑容里,充满了赞赏和激动。
“说得好!编户齐民,统一管辖!将军,您这八个字,就说出了宋公您远胜汉高祖的根本所在!”
他转向刘裕,声音陡然变得激昂起来,像一把出鞘的宝剑,锋芒毕露:“汉高祖得天下,靠的是一个‘分’字!他把大片的土地和人口,像分猪肉一样,分给了韩信、彭越、英布。他像一个慷慨的家主,把辛辛苦苦挣来的家产,分给了几个最得力的儿子和伙计。他得到的,只是一个名义上的天下,一个靠着利益和人情维系的松散联盟。所以他的后半生,都活在对这些异姓王的恐惧之中,他要费尽心机,把分出去的东西,再一块一块地收回来。这个过程,充满了血腥、阴谋和背叛。汉家天下四百年,从头到尾,都在跟地方的豪强、外戚、权臣作斗争。其根源,就在于高祖皇帝开国之时,定下的这个‘分’字!”
“高祖,是先破坏,再建设。他先把秦朝建立的天下秩序打得稀巴烂,然后再用分封的办法,勉强把它粘合起来。这是一种对现实的妥协,是一种权宜之计。”
“而宋公您呢?”慕容平的眼睛里,闪烁着一种奇异的光芒,那是智者洞悉天机、勘破迷雾的光芒。
“您从京口起兵,打桓玄,灭卢循,伐南燕,您每到一处,做的第一件事,就是‘土断’!”
“土断”这两个字一出口,刘裕的身子,猛地一震!那只悬在半空的手,也微微颤抖了一下。
这才是他真正的根基所在,是他与盘踞江东百年的门阀世家斗争的核心!将那些从北方南渡的侨姓士族,与当地的吴姓士族一样,就地编入户籍,一体纳税服役。这等于是在挖那些高门大族的根!他们之所以能超然物外,世代簪缨,靠的就是他们拥有无数不向国家纳税的荫客,拥有不为国家服役的部曲,他们是一个个独立于国家之外的经济王国。
而刘裕要做的,就是把这些特权,统统打碎,把权力从世家大族的手里,收归国有!
慕容平的声音,像一声声重锤,狠狠地敲打在在场每一个人的心上。
“您把那些藏在豪门大宅里,不见于国家图籍的荫客、佃户,重新编入国家的户册,让他们成为您的士兵,成为您税收的来源!您把那些被世家大族巧取豪夺、霸占了上百年的无主山林、湖泊、土地,重新丈量,分给那些真正耕种的农民!您不是在‘分’,您是在‘收’!是在‘统’!”
“汉高祖是把一个完整的天下,打碎了分给众人。而您,是把一个已经破碎不堪、四分五裂的天下,一块一块地重新拼凑起来,用您的意志和铁血,把它熔铸成一个真正统一、高效的整体!您走的,是一条比汉高祖艰难百倍,但也要高明百倍、伟大百倍的道路!”
“高祖的胜利,是他个人和他那几个伙伴的胜利。而您的胜利,将是一种制度的胜利!您在建立一个前所未有的,真正中央集权的强大国家!在这个国家里,没有可以和朝廷分庭抗礼的封国,没有可以藏匿人口不交税的豪门。所有的土地,所有的人口,都将直接掌握在君主一个人的手中!”
“这,才是帝王真正的权柄!这,才是万世不移的基业!汉高祖给了功臣王位,却给自己和后世子孙留下了无穷无尽的祸患。而您,看似对手下将士‘吝啬’,不封王,不裂土,但您要给他们的,是一个稳定、强大、能够荫庇他们子孙后代百年的统一王朝!您要给这片土地上所有百姓的,是一个崭新的、公平的秩序!”
慕容平向前踏出一步,昂首挺胸,用尽全身的力气,发出了最后的呐喊:
“试问宋公,这样的功业,这样深远宏大的谋划,是那个只懂得‘大块吃肉,大碗喝酒’,用分封来换取一时忠诚的汉高祖,所能想象,所能比拟的吗?他若泉下有知,看到您今日所为,是会嘲笑您,还是会羡慕您,甚至……会嫉妒您?!”
慕容平说完了。
每一个字,都像一颗烧红的铁钉,钉入了刘裕的灵魂深处。
如果说他之前的话,是把刘裕从云端拉下凡尘。那么现在,他就是亲手为刘裕,铸造了一座通往不朽神坛的阶梯。
他没有否认刘裕的那些“不如”,反而把那些“不如”,都解释成了更高明、更伟大的铺垫。
你的时势更艰难?那是因为你在做一件开天辟地、前无古人的大事。
你用人唯下,不敢放权?那是因为你所建立的这套制度,不需要权臣,不需要伙伴,只需要最忠诚、最高效的执行者。
你格局“小”,不肯分封?那是因为你的目标,是建立一个权力高度集中、远超汉唐的,前所未有的强大帝国!
这番话,像一道开天辟地的闪电,瞬间劈开了刘裕心中所有的迷雾和困惑。
他一直觉得自己和史书上那些开国帝王不一样。他总觉得自己的路,走得特别累,特别孤独。他要面对的掣肘太多,他能真正依靠的人太少。他像一个背着沉重石磨的巨人,在泥泞和荆棘中艰难前行,每一步都踩出血印。
现在,慕容平告诉他:你之所以累,是因为你在开辟一条全新的道路。你之所以孤独,是因为你走在了所有人的前面,你的背影,就是这个时代的丰碑。
他那些不近人情,甚至被外人诟病为“刻薄寡恩”的手段,比如对部下近乎偏执的控制,对土地和人口近乎贪婪的占有欲,在这一刻,都有了最合理、最宏大、最光辉的解释。
他不是一个单纯的武夫,一个野心勃勃的权臣。
他是一个……制度的创建者。一个新秩序的奠基人。
刘裕那只紧握的拳头,不知不觉间,已经松开了。
他胸中那股即将喷发的怒火,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取而代之的,是一种难以言喻的狂喜。那不是打了胜仗的狂喜,不是得了金银财宝的狂喜。
那是一种被人真正理解,被人点破天机,灵魂在瞬间得到升华的,巨大而深刻的喜悦!
千金易得,知己难求。
他看着慕容平,这个亡国的俘虏,这个刚刚还在他刀口下讨生活的人。眼神里,再也没有一丝一毫的杀气。
那眼神,变得像一个在沙漠中跋涉了三天三夜、濒临死亡的旅人,忽然看到了一片望不到边际的绿洲。像一个在狂风暴雨的黑夜里迷航的水手,忽然看到了远处灯塔射来的,那道穿透一切黑暗的光芒。
“哈哈……哈哈哈哈哈哈!”

刘裕再次大笑起来。
这一次的笑声,不再有愤怒,不再有压抑。笑声洪亮、高亢、充满了淋漓尽致的畅快和酣畅。他一边笑,一边用手指着慕容平,嘴唇翕动,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,仿佛世间所有的言语,都无法表达他此刻万分之一的心情。
帐下的将军们,全都看呆了。
他们看着宋公那张因为狂喜而显得有些扭曲的脸,再看看那个衣衫褴褛却傲然挺立的慕容平,脑子里一片空白,仿佛被重锤砸过。
他们听懂了慕容平的每一句话,但又好像没完全听懂。他们只知道,这个俘虏,用几句话,就让一头即将暴怒的雄狮,变成了一只手舞足蹈的羔羊。
这比在万军丛中,取上将首级,还要不可思议。
05
刘裕的笑声,在大帐里回荡了很久很久,才渐渐平息。
他站起身,亲自走下帅位,一步一步地,走到了慕容平的面前。这个动作,让所有的将军都倒吸了一口凉气,下意识地站直了身体。
刘裕的身材异常高大魁梧,站在清瘦的慕容平面前,像一座移动的铁塔,投下的阴影几乎能将对方完全笼罩。他低着头,看着这个比自己矮了一个头的亡国之臣,眼神里,是前所未有的欣赏、热切和尊重。
“先生一席话,令我茅塞顿开,胜读十年兵书,胜过十年苦思!”刘裕的声音里,充满了不加掩饰的真诚,“我刘裕征战半生,自问识人无数,却不想,天下最懂我的人,竟然在敌营之中。惭愧,实在是惭愧啊!”
说罢,他对着慕容平,这个衣衫破烂的阶下之囚,深深地、郑重地,行了一个大揖。
这一揖,重如泰山。
慕容平大惊失色,连忙侧身避开,不敢受此大礼,慌忙躬身回拜:“宋公折煞草民了!草民不过是亡国之人,纸上谈兵,胡言乱语,万不敢当此重礼!”
“不!”刘裕上前一步,一把扶住他的双臂,双手紧紧地握着他的肩膀,那力气大得让慕容平感到一阵骨头欲裂的疼痛,但更多的是一种发自内心的震撼。
“你不是纸上谈兵!”刘裕的眼睛亮得吓人,像两团燃烧的火焰,“你说的是经国大道!是帝王心术!我过去只知道埋头砍杀,只知道一寸一寸地争夺土地,却从未想过,我做的这一切,连在一起,竟是如此一副波澜壮阔、前无古人的图景!”
他转过身,面对着帐中所有跟随他出生入死的心腹爱将,朗声道:“你们都听到了吗?”
王镇恶、檀道济等人,连忙躬身应道:“末将等愚钝,领会不深。”
“不是你们愚钝,是我自己,也一直身在局中,未能看清全貌!”刘裕的声音里,带着一丝如释重负的感慨,“我一直拿自己和汉高祖比,总觉得他运气好,我本事大,心里始终憋着一股劲,不服气。今日听先生一言,我才豁然开朗,我与他,根本就不是一条路上的人!他是旧时代的终结者,而我,要做一个新时代的开创者!”
“传我将令!”刘裕的声音,陡然变得威严无比,充满了不容置疑的决断。
“在!”帐外亲兵齐声应诺。
“为慕容先生松绑,赐座,上最好的酒肉!从今日起,慕容平先生,便是我宋公帐下的参军,参赞军机,凡军国大事,皆可与议!”
这个任命,如同一块巨石投入平静的湖面,让所有人都再次震惊。
一个刚刚还跪在地上、生死悬于一线的阶下囚,转眼之间,就成了宋公的幕僚,可以参赞军机。这个身份的转变,比坐火箭还快,比战场上的任何一次奇袭都让人感到不可思议。
慕容平自己也愣住了。他本以为,能保住一条性命,已是万幸。却没想到,刘裕竟给了他如此高的礼遇和信任。
“宋公,这……这万万不可。”慕容平连忙推辞道,“草民乃戴罪之身,又是鲜卑慕容之后,何德何能,敢居此高位……”
“先生不必多言!”刘裕打断了他,态度无比坚决,“我刘裕用人,不看出身,不问过往,只看才能!你有经天纬地之才,若只让你做一个默默无闻的俘虏,那是我的罪过,是天下的损失!”
他拉着慕容平的手,无视对方手上的污垢和粗糙,亲自把他引到自己的帅案旁边,大声命令亲兵:“加座!就在我身边!”
这个位置,比王镇恶、檀道济等所有核心大将的位置,都要靠近刘裕。
亲疏远近,高下立判。
王镇恶看着这一幕,脸上的肌肉抽动了几下。他心里有些不是滋味,像是自己珍藏多年的宝贝被一个外人抢了风头。但更多的,是一种由衷的敬畏。他终于明白,自己和宋公的差距到底在哪里了。自己只会凭着一身蛮力和血勇去杀人、去占地,而宋公,却能从敌人的几句话里,发现治国安邦的宝藏,发现一个能为自己擘画未来的大才。
这种胸襟,这种气魄,才是真正的帝王胸襟。
酒宴继续。
但气氛,已经完全不同了。
之前的喧闹、粗豪、放浪形骸,都消失了。取而代之的,是一种带着敬畏的庄重和肃然。将军们喝酒说话的声音,都小了很多。他们不时地,用复杂的眼神,瞟向那个坐在宋公身边,从容地与宋公低声交谈的清瘦文士。
刘裕频频向慕容平敬酒,向他请教各种问题。从北方的风土人情,到后秦、北魏的内部虚实,再到如何安置流民、发展农桑的长远之策。
慕容平对答如流,他的每一句话,都仿佛说到了刘裕的心坎里,解开了他心中积存已久的许多困惑。两人越谈越是投机,大有相见恨晚之感。
夜,终于深了。
宴席散去。将军们带着满腹的心事,和一身的酒气,各自回营。
刘裕亲自将慕容平送至为他安排的崭新营帐,看着他进去,才转身离开。
他没有直接回自己的主帅大帐,而是独自一人,缓步走上了一处高坡。
秋夜的风,已经很凉了,吹在脸上,带着一股草木枯萎的萧瑟气息,也吹散了他身上的酒意。
他抬头,看着天上的那轮明月。
月光如水银,静静地流淌下来,洒在连绵不绝的营帐上,洒在那些冰冷的刀枪剑戟上,像给这片杀气腾腾的土地,披上了一层温柔而悲悯的轻纱。
四百多年前,那个叫刘邦的泗水亭长,是不是也曾在某一个胜利的夜晚,这样孤独地看着月亮,想着自己的心事?
刘裕的嘴角,缓缓浮现出一丝淡然的微笑。
他不再去想自己和刘邦孰强孰弱了。
这个问题,已经没有了任何意义。
他知道,自己脚下的路,是一条从未有人走过的路。这条路会更艰难,更孤独,充满了更多的荆棘和险阻。
但他不害怕。

因为今晚,他终于无比清晰地看清了这条路的终点,屹立着的,是怎样一座雄伟壮丽的丰碑。
他不再是一个单纯为了权力和欲望而战斗的武夫。
他是一个开创者。
他要用自己的刀,自己的剑,为这个纷乱了百年的天下,重新‘统’一起来,建立一个真正属于他刘裕的,崭新的秩序。
一阵凛冽的夜风吹过,卷起他身后的玄色披风,在空中猎猎作响,如同一面展开的战旗。
他的身影,在清冷的月光下,被拉得很长很长,像一尊即将从黑暗中走出的,不朽的雕像。
加杠杆炒股票.配资投资平台.股市五倍杠杆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